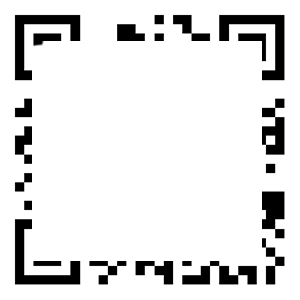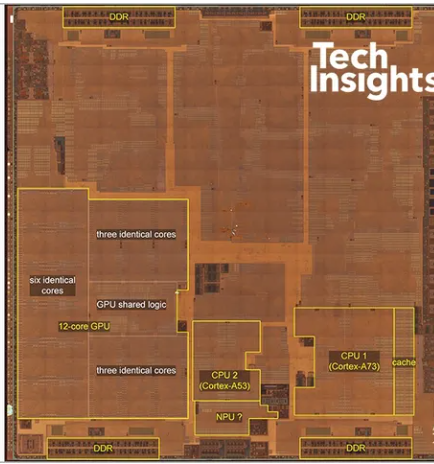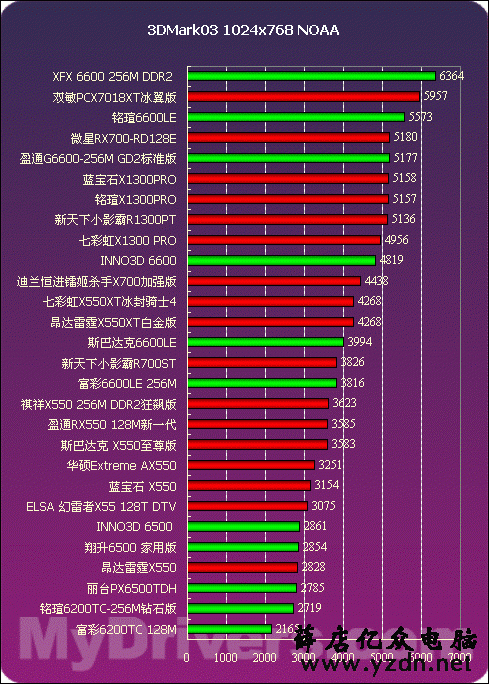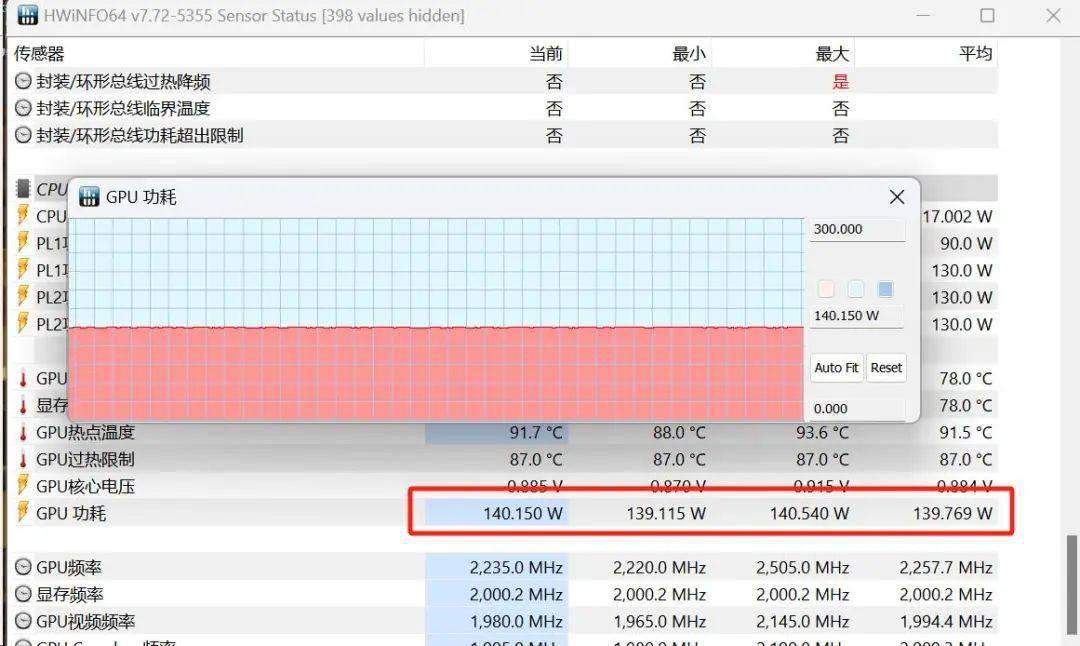杨荣国简介(历史学家杨国荣简介)
杨荣国简介(历史学家杨国荣简介),本文通过数据整理汇集了杨荣国简介(历史学家杨国荣简介)相关信息,下面一起看看。
基于“事物”的世界
作者: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院哲学系)
来源:《哲学研究》 2016年第11期
时间:孔子,2568,丁酉,3月9日,任旭。
耶稣2017年4月5日
[摘要]
作为抛弃原始形态的存在,现实世界是由“物”构成的。广义的“物”可以理解为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从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与“物”无关的东西,似乎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但是,以现实世界为方向,“物”就有了更原始的意义。人们通过事物来处理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物的关系是以人与物的关系为中介的。“物”只有融入到“物”中,才能显示出其多样的意义。人类活动(“事件”)形成的现实世界,既表现为事实世界,也表现为价值世界,“事件”从本源上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统一提供了基础。在认识现实世界的过程中,既要避免把“物”变成“心”,也要避免把“物”当成“言”。肯定现实世界是以“物”为基础的,不仅意味着扬弃存在的性质,而且意味着承诺的现实性。
[关键词:]
现实世界/自然世界/“事物”/“事物”
[正文]
与自然存在不同,现实世界是由“物”构成的。人是通过“物”来处理“物”的,“物”是在做事的过程中被把握和规定的。“物”的展开过程,也是“物”的意义不断呈现的过程。由“物”生成的世界体现为人的世界或人化的存在,其固有特征是既涉及事实世界,又涉及价值世界。关注世界的现实,同时避免把事物变成心或文字。以“物”为本源,现实世界既抛弃了存在的真实性,又确认了其真实性。
什么是“东西”?综上所述,“物”可以理解为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人的活动是广义的人的“做”,所谓“做事,做事”(《韩非子喻老》)。从这个意义上说,“做事”一开始就是和“自然”相对的。荀子曾简洁明了地指出这一点:“无为而无不为。”(《荀子正名》)“物”表现的是人类的作用,“自然”则是人类没有参与其中。所以,事物和自然构成对立的两端,而事物和自然又是相互一致的。在荀子看来,自然的本性仍然在人的作用之外,其特点是自然而不涉“物”。以上对“物”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物”与人及其活动的关系。从赞美天地的培育,到经济、政治、伦理、科学、艺术等活动,“物”发展为多重形态。推而广之,人的活动既与行为有关,也与知识有关,因此,广义的“物”也包括知识和行为。
上述视域中的“事物”首先是一个动态过程,它可以进一步导致事物和事件。而事物和事件则表现为人类活动的结果。与“不是自然发生的事情”不同,事物是经过人的影响,打上不同标记的物体。这类物体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导向,表现出各种形态。事物在广义上也指综合的社会现象,如“旧事物”、“新事物”。这几种东西也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在由“物”引起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相对于事物的具体产物或结果,事件更多地表现为已完成的行为过程,可以由单个行为过程组成,也可以由已经发生的一系列行为组成,其内容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事件作为一个完整的行为过程,离不开人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事件需要与所谓的“物理事件”区分开来:物理事件如果发生在人类的作用之外,就可以被视为自然现象,比如云本身相互作用产生的雷电;如果物理事件发生在实验条件下,就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而是融入“物”,成为涉及人的广义事件的构成。
“物”的对立面是“物”,“物”首先表现为与人对立。055-79000曾指出:“万物皆有终,万物皆有始。如果你知道事情发生的顺序,你就会走捷径。”“物有其源有其终”从本体论上讲,着眼于“物”本身的本体结构;“万物有始”是指就人的活动而言,主要着眼于实践的顺序。本体是客观规律,而实践的顺序与人自身的活动过程有关。两者都有各自的规则,但又相互关联。所谓“知事之序”,就是要把握“事”与“物”的本质关系,从而达到从事到“物”。在《大学》看来,把握“物”与“物”的不同规定和相互关系,是顺应道的前提。从这种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上述论域中的“物”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尚未进入人们认识和行动领域的对象,这种形态中的“物”可视为自然存在;二是已经进入知行领域的对象。“物”的这种形式在中国哲学中接近于“场所”,其特点是与人形成了客观的关系,具体表现为“用势之人尽快”。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如何避免人的物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这种追问的逻辑前提就是人与“物”的区别。当然,后面会进一步讨论,与人相对的“物”也可以作为人的活动进入做事的过程,通过人的作用(做事)的过程成为物。事实上,作为人的活动结果的事物,往往同时基于人对“事物”的行动(做事)过程,与之相关的事物也相应地表现出“事物”的转化形式。
在海德格尔的《大学》一书中,他区分了“物”这个词所代表的不同对象,它包括:那些可以被触摸、达到或看到的,即手边的东西;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下,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康德的自在之物。(海德格尔,第5页)这种观点注意到,广义的事物既包括原初的存在(如事物本身),也包括已经进入知行领域的对象(手边的事物)。然而,将“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归类为“事物”,表明海德格尔未能对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实质性区别给予足够的重视。如前所述,“物”首先表现为人的实践活动,正是这种规定使其区别于作为人的行动对象的物。事物的上述内涵似乎超出了海德格尔的视野,事物之间界限的模糊不仅限制了对事物的理解,也限制了对事物的把握。
现实来源于“物”。这里的现实世界不同于原本的存在,而是呈现给人们不同意义的现实。这个视野中的现实世界,从魏的名句“春潮迟来雨,野渡无人过江”(《何为物》)中有其特定的含义。其实,诗中的“无人”是以“有人”为前提的:《野渡无人》所表现的只是人的暂时缺席,其情形与人类出现之前的蛮荒世界不同。洪水世界可能有“春潮”和“雨”,但既没有“野渡”,也没有“舟渡”:野渡和舟渡存在于人做事的现实世界中。从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与“物”无关的东西,似乎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但是,以现实世界为方向,“物”就有了更原始的意义。作为抛弃原初形态的存在,现实世界处处打上了人的印记;人们不仅生活在其中,而且参与了它的形成过程。所谓“颂天地之修”就体现了这一点。
从“颂天地之修”的角度看,“物”是通过“物”进入现实世界的。正是在人们做事的过程中,与人无关的“物”开始成为人们行动的对象,从而参与到现实世界的形成过程中。除了“物”之外,“物”当然是存在的,只是它们的意义隐藏起来却不明显。只有在做事(包括科研活动或广义的认知活动)中,“事”的不同含义才能逐渐打开。相对于人而言,意义的具体内涵既涉及价值-目的,也涉及认知-理解。做事的过程不仅在评价层面上表现出“物”对人类的价值意义,而且在事实层面上表现出“物”的认知意义。从宏观领域新天体的确定到微观领域基本粒子的发现,“物”进入现实世界与人做事的过程(包括不同领域的科学探索活动)密不可分。
广义来说,“存在什么”?“事物以何种方式存在”?这是质疑存在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上的形而上学往往以思辨的方式回应这些问题,这种意义上的“物”往往表现为思辨的结构。在现实中,上述这类问题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但它们的解决与在形而上学领域中做事的过程是分不开的。从日常生活到其他领域,在人们从事的各种活动中把握“物”的外在形式和内在规定。可见,“物”对做事的过程是开放的,其属性、功能和存在方式也是在做事的过程中被把握和规定的。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物”的规定,即“物”成为人类行动的对象后,并不是完全自在或既定的:通过做事,人们可以赋予“物”更多样的存在形式。
人们通过事物来处理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物的关系是以人与物的关系为中介的。“物”只有融入到“物”中,才能显示其多样的意义;“物”的展开过程,也是“物”的意义不断呈现的过程。以“做”或“做”的形式,“事”也包括人对“事”的行动。从认知层面来说,通过这个动作,事物“本来面目”的性格从隐藏中显露出来;就评价而言,通过这个功能,也呈现出了“事物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的趋势。所谓“不是什么”,就是事物对人的价值意义。这种意义不是事物的原初规定性,而是在做事的过程中生成和表现出来的:当事物与人的需要相一致时,其价值意义就会呈现出来,通过人的做事,事物所包含的价值意义就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在谈到治国之道和君子的特质时,荀子曾指出:“夫以德定,则量能而为之,使一切有德之人各得其所。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的官位吗?各就各位,各就各位。谨慎和墨迹不应该被允许谈论它。惠施和邓不敢偷偷进入他们的谈话,但他们应该把他们的话视为理所当然,做他们应该做的一切。是的,然后君子的长处也是。(《滁州西涧》)这里还涉及到“物”与“物”的区别:“物”不同于人的活动(物),而是人的行动的对象;“物”作为人类活动所面对的对象,有恰当或不恰当的问题。所谓“万物各得其所”,就是通过人的活动,将不同的物体进行适当的放置。另一方面,“物”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事当如是”,表明人的活动过程中所涉及的一切问题都得到了合理的处理,而“事当如是”则进一步强调一个人所做的事必须是遵循的、自然的。在这里,“物”主要是作为客观存在而出现的,而“物”不能脱离人自身的存在;物”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但是否“恰当”取决于人(物)行动的过程。
从哲学史上看,理解“物”与“物”的关系有不同的进路。首先,“物”是由“物”来诠释的,体现在郑玄对“物”的诠释中:“物还是物。”(《荀子儒效》)这个定义被崛起的哲学家们反复认可。从朱到王阳明、王夫之,大部分儒家哲学都继承了这一阐释方向。《礼记注大学》还可以看到以物(人的活动)认识物的趋势:物属于人所从事的活动,物的具体内容是人的作用和活动,而物是开放的(物是对象,作用于物)。不难看出,这里体现的是“物”(自然物)与“物”(人的活动)之间的交流,同时也赋予了事物更原始的性质。
与上述做法相比,另一种哲学倾向更侧重于“物”与“物”的区别,这一点从庄子的相关论述中可以更具体地看出。庄子在谈及圣贤时指出:“圣人不搞事,不图利,不图害,不求理所当然。”(《易传》)“不务正业”,即不参与人的各种活动(“物”),“不利不害”是对超越价值的追求,二者都体现了“物无自然”:“不务正业”就是远离物,“不利不害”就是对价值的追求。对“物”的疏离,对应的是对自然的崇拜。在天人之分上,庄子的基本思想是“人不可毁天”,这一思想优先于自然原则。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物”的原初形态更多的是与自然相关。从自然的原理来看,庄子显然很难对旨在改变“物”的自然规则的“物”持肯定态度:“不以物为物”与“人不可灭天”是一致的,其本质在于维护自然之物,排斥人为之物,而“物”所形成的现实世界则是如此
就“物”与“物”的区分而言,“物”对“物”的解释表明了物与人的关系:只有进入人的活动(“物”)的过程,“物”才能敞开并获得其意义;“不以物为物”重点在于物与人的区别:从存在形式上看,自然之物是人的活动领域(物)之外的。前者当然可以通过事物来把握事物,而后者则确认事物的原初形态是原初的,它们从不同的侧面突出了事物的内在品格。当然,仅以“物”来解释“物”,可能会因为在理论上过分强化人的作用而削弱现实世界的现实性;单纯强调“不以物为物”,将事物悬置起来,很难落实世界的现实品格。
在现代哲学中,维特根斯坦曾经强调过“事实”和“事物”的区别。《庄子齐物论》年初,维特根斯坦指出:“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维特根斯坦,第25页)这里的重点是区分“事实”和“事物”。“事实”可以看作是进入人们认识和行动领域的对象,但它不同于表现为人的活动的“事务”:事实更多地表现为人的活动的结果。这样,当维特根斯坦强调“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时,他当然注意到了现实世界不同于与人无关的“事物”,但却未能对更原始意义上的“事物”给予充分的关注。从历史上看,人们在广义的做事过程中作用于“物”,把原来的“物”变成“事实”。与此相关,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事实”,还需要关注更原始意义上的“事件”,以理解现实世界。尽管后期维特根斯坦注意到了日常行为在语言理解中的作用,但他早期的思想仅仅局限于“事物”是“事实”的论证,这无疑使他难以真正到达现实世界。
“物”表现的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这些活动是在“物”的现实世界中产生的,相应地不能脱离人的所作所为。做事的过程涉及到对“事”的行动。通过这一行动,人同时在“物”所构成的世界中打上了自己的印记,而现实世界则体现为一个人的世界或一个人化的存在。
基于“物”的现实世界首先与事实相关。如前所述,事实不同于自然之物,但它是进入知行领域的对象。作为人类行动的产物,现实世界中的存在首先表现为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非人类行动之外的“物”。就事实与“物”的区别而言,现实世界也可以视为事实的世界。
从认识世界的角度看,事实世界涉及科学世界图景。从狭义上讲,事实往往与科学认知有关,科学世界图景首先是通过事实展现出来的。科学作为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不同于思辨建构或思辨演绎,它以事实为出发点。从形式层面来说,借助实验和数学方法,科学对世界的认识不同于纯粹的现象观察,而更具有理论性。它所展示的世界秩序也不同于日常经验的秩序,它通过理论和逻辑活动展示一种存在的结构,这种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感性直观相异化的。但以科学的概念、数学模型等为框架,科学在更深、更内在的层面上展现了世界的秩序。归根结底,这种顺序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并显示了事实之间的关系。
“物”作为人的活动,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与事实相关,而且包含了价值的维度。与之相联系的,以“物”为基础的现实世界,既是与“是”相对立的事实,也是其价值的维度。换句话说,它既是一个事实世界,也是一个价值世界。从广义上讲,对价值的追求及其结果体现在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人在活着的过程中,总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需求。但是,自然的东西不会主动适应人,也不会自发满足人的需求。自然的对象只有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世界,才能获得“为我”的本性。事实上,作为人的活动,“物”的作用之一就是使舒适的对象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所用的东西”,后者也表现为价值场的存在。从早期的渔猎采集到现代高科技领域的生产活动,广义的“物”不仅改变了世界和人本身,也从源头层面赋予了世界价值。
价值世界不仅以人化的形式表现为对象世界,而且在社会领域表现为社会现实。后者与自然物的区别在于,它的形成和功能都与人的“存在”有关。在对象进入知行领域之前,它就呈现出原初的形态,而社会现实在上述领域中并不具有原初的性质:它是在人的知行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存在与人的行过程密不可分。与客观世界一样,社会现实具有多种形式,包括系统、组织、交流社区和相关活动。后者展现了社会历史的内涵,呈现出更加稳定的特征。
人的存在过程总是伴随着价值的关注,存在的价值意义在人的存在过程中得到了更加具体和多样的表现。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关注人的存在,其考察也涉及价值的内涵。总的来说,海德格尔把人的存在看作是一个死亡的过程。对他来说,人类虽然有自我规划的能力,但其存在的形式相应地不是既定的、固有的,而是对未来开放的。但他们的生活过程总是难以摆脱烦恼、烦恼等体验。同时,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往往处于沉沦之中,很难到达真实的自我。个体只有在对死亡的恐惧中,才能真正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替代性,从而回归真实的自我。上述观点的要点在于将人的生存过程与烦恼、恐惧联系起来,以对死亡的第一次体验作为确认个体存在价值的前提。无论从生活的实际情况,还是从自我的情感体验来看,上述意义上的烦恼和恐惧都有一些负面的意义。以上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当然包含了价值的维度,但这种价值关注同时缺乏积极向上的内涵。
与海德格尔以不知死,如何知生来理解存在的过程不同,中国哲学更侧重于“未知生,如何知死”(《逻辑哲学论》),其中包含着对生的强调:“生易”(《论语先进》)和“天地由德而生”(《周易系辞上》)。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说,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与死亡的意义相比,生命不仅包含了各种发展可能性,还面临着广阔的意义空间。在人的存在过程中,生命的延续伴随着人自身的创造性活动。这种创造性活动不仅改变了对象,而且赋予了人存在的意义。虽然个体的存在确实是不可复制和不可替代的,但人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内在力量,还可以对世界进行创造性的改变(立功),培养和提升自己的人格(向善),在文化上承上启下(立言)等。从这个角度来说,真正的存在不是接近或经历死亡,而是对生命的认知和对生命意义的自我实现。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存在”相比,中国肯定“未知生,如何知死”的哲学似乎更深入地切入了存在的意义。
从个体存在的具体过程来看,产生烦恼和恐惧无疑是有现实来源的,个体本身也经常经历这种情绪体验。海德格尔对此的描述显然是细致而深入的。但是,无论是对待事物还是对待人,人存在的过程都不是简单的消极或否定。就处理事物而言,如前所述,人与物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人通过作用于对象,创造性地改变世界,使之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作为一个涉及人的创造性活动的过程,人与物的相互作用不仅包含积极的、建设性的内容,而且能使人感受到自身本质力量的外化,从而获得审美体验。同样,个体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并不像海德格尔所想的那样,只是沉沦于大众或者走向普通人,而是同时处处都能感受到人性的光辉。通过主体间的理性对话、理解和沟通,人们会倾向于不断化解可能出现的紧张和冲突,逐渐建立合理的沟通关系,这不仅赋予了人们独立的意识,也印证了人性平等的理念。更何况,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不仅涉及理性的沟通,更涉及情感的交流。从亲情到友情,从传统的仁爱到现代社会的人文关怀,人际交往在很多方面都涉及情感维度。这种情感是否可以作为本体(所谓“情感本体”)当然可以讨论。然而,基于情感交流,以更广泛意义上的亲情、友情、仁爱等形式呈现的情感体验,确实是人类整个生命过程中所固有的,也确实展现了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人类存在的这种情感维度,显然不能简单归类为“烦恼”、“沉沦”或失去真我。其实应该理解为真实自我的内在体现。在上述的情感交流和体验中,人们也从正面感受到了存在的意义。
做事情涉及很多方面,从策划运营到过程中的协调。做事总是忙忙碌碌。然而,“事”并不仅仅指烦恼和忙碌。从历史上看,人类在做事的过程中,不仅创造了各种文化成果,也使自己超越了仅仅为了生存而做事:随着必要劳动时间的逐渐缩短,人类做事的领域不断突破生产劳动,获得了越来越多样和广阔的形式。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从科学研究到艺术创作,人们做事的过程总是忙忙碌碌,但同时又不断摆脱不同形式的强制,走向自由。再者,人的真实存在总是在忙碌与轻松的互动中发展。就做事的过程而言,它的展开过程往往伴随着放松的节奏,而这种轻松适度的操作方式本身也体现了忙碌与放松的互动。现代社会,自由时间的增加,为生存过程中的闲暇和休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工作和休闲经常交织在一起。总之,“物”内的放松程度和“物”外的休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人的生存过程的多维性,其中蕴含着多种价值意蕴。
可见,科学图景所开启的事实世界和生存过程所展示的价值世界,构成了基于“物”的现实世界的不同维度。作为现实世界的不同规定,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区别包含着单向发展的可能性。事实上,在历史上,这两者往往被视为对立的领域:在这个视野中,事实世界与真理相关,而价值世界与善相关,两者之间更多的是割裂。在从自然事物向事实世界转化的前提下,科学图景首先将世界还原为数学、物理、化学等。在事实世界中,世界是以数学等可以处理的形式呈现的。而数学和逻辑以外的属性往往被隐藏起来,从而呈现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诗意的光辉,而相关的存在过程往往倾向于认同真理,疏远善。事实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真实的,真实的反面当然是。以实现目的和理想为方向,对善的追求同时表现出对自然的关注,而价值圈往往被视为一种超越现实的存在状态或理想(当然)。在超越现实的同时,不仅价值世界本身的现实基础容易被悬置,而且对善的确认也常常与对真理的探求相隔绝。虽然单向的价值追求看似涉及“真”,如海德格尔的理想自我与真实自我的联系,但这种“真”往往与现实的存在形式相去甚远:在海德格尔看来,通过退出共存、先体验死亡而达到的“真实”自我,本身就是一种缺乏现实的抽象存在形式。
相对于事实价值、真与善、现实与自然,从休谟开始的“存在”与“应当”的区分,以及更广义的科学与人文的对抗,都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以事实为导向的科学领域和追求人文价值的文化领域往往形成各自封闭的文化边界,彼此难以理解和沟通,逐渐形成文化鸿沟。这种文化分离还体现在不同哲学思想的交锋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分歧就表明了这一点。就个体而言,上述分裂和对抗导致了内心精神世界的简单化和片面性,使得个体往往接受数学和符号构成的世界图景,或者认同诗歌的意境;每一个都对应着数学和诗歌的演变。
抛弃上述对抗,需要回到以“物”为基础的现实世界。如前所述,人类活动形成的现实世界(“物”)既表现为事实世界,也表现为价值世界。广义的现实世界是世界的人化,这个世界的建构不仅仅局限于事实认知,也不单纯表现为价值评价。人类存在的过程总是包含着多种需求,驱动人们从事各种活动(做事)的正是后者,而“事”的发展既需要基于事实的认知,也需要价值的评价:如果价值的评价规定了人们应该做什么,那么对事实的认知就制约了人们如何去做;前者关系到做事的价值方向和目标,后者关系到做事的方式和程序。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做事既关系到合法性,也关系到有效性。“物”的正当性基于自然(体现一种合理的价值方向),而物的有效性基于现实(符合存在规律)。在将自然世界转变为人化世界的过程中,事实认知和价值评价从不同方面为人们提供指导,并由此保证“物”本身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由此产生的现实世界表现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统一。不难看出,在这里,“物”从本源上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统一提供了基础。
现实是由“物”构成的,这使它不同于原本的存在。然而,从历史上看,尽管现实世界的生成性在哲学上得到了肯定,但在如何理解现实世界的生成性或非自然性上却存在不同的进路。
众所周知,康德区分了现象和自在之物。从自然与现实的区别来看,自在之物存在于知行过程之外,属于自然,而现象进入了人类的认识领域,从而超越了自然,获得了现实的品格。对康德来说,现象的出现是以人类先天的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作用于感性材料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象本身具有被建构的性质。可见,在康德看来,现象已经抛弃了本质,进入了广阔的现实世界;现象的这种现实性格不是既定的,而是由先天的认知形式规定的。这种观点无疑从现象层面注意到了现实世界的不真实感。但同时,康德强调现象的非自然性主要来源于先天的认知形式。这种抽象的先天形式明显不同于作为人的现实活动的“物”,它对现象的规定也不同于由“物”引起的规定。
黑格尔对世界的理解也不同于它原本的存在。如前所述,康德在区分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前提下,只确认了现象的不现实性。另一方面,黑格尔把绝对精神作为第一原则,并赋予这种精神以动力,肯定它可以通过其外化在自然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生成世界。对于黑格尔来说,精神外化为自然和世界,不仅给了自然和世界以坚实的基础,而且抛弃了世界和精神的分离。黑格尔虽然以精神为本源,但他对自然和世界实在性的肯定无疑不同于贝克勒对世界真理的怀疑,他对世界和精神分离的扬弃表现出试图超越近代以来心物对立、天人对立的趋势。黑格尔所理解的绝对精神,就其本质而言,可以看作是人的观念和精神的形而上的、思辨的。以这种精神作为自然和世界的源泉,在某种意义上也以思辨的方式触及了现实世界的生成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在黑格尔看来,精神本身作为存在的基础,是思辨和抽象的产物,不同于人的现实精神。以形而上学和思辨精神为前提的自然和世界的生成,不同于自然存在,而缺乏以“物”为基础的世界的人化现实。黑格尔在肯定精神外化的同时,强调随着自然、社会和人的概念的发展,精神最终回归自身。这种始于精神,终于精神的进化过程,显然远远不是通过人的现实活动(“物”)来赞美天地的教育。
如前所述,海德格尔提出了基本本体论,关注个体的生存。在海德格尔看来,个体不是被规定的既定存在,而是包含着面向未来的不同可能性,这为个体生存过程中的自我规划提供了前提。个体的存在与广义的生活世界相关。把个体的存在过程理解为一个自我规划或自我计划的过程,同时意味着把生活世界的发展与自身的活动联系起来。然而,海德格尔所说的计划或密谋,基本上仅限于观念的领域。这种概念活动,显然不同于作用于并实际改变对象的“物”。在海德格尔看来,个体的生存过程也是以烦恼、恐惧等心理体验为具体内容的。如果说策划和密谋主要是从概念层面反映个体存在的自主性,那么烦恼和恐惧体验更多的是表现个体内心的精神世界,两者都没有超出概念领域。与作用于对象并实际改变对象的活动相比,无论是人的计划与规划,还是烦恼与恐惧的体验,都属于广义的“心”。从本质上说,海德格尔对人的生存过程和生活世界的理解,其特点是在“心”中见,而不在“物”中见。他的关注主要局限于人的存在意识或精神维度,而人的实际工作过程基本上处于。
绝对精神的外化首先与外部世界有关;个体意识的活动涉及到与人的生存过程相关的生活世界。两者都局限于广义的“心”,同时又承诺与原初存在不同。在现代哲学中,对世界的非现实性的另一种理解方式体现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上。随着所谓的语言学转向的出现,从语言层面理解世界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维特根斯坦在肯定“世界是事实而不是事物的总和”的同时,强调“语言(我所理解的唯一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边界。”(维特根斯坦,第79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语言与世界边界的联系。从逻辑上讲,把语言定义为世界的边界,说明人所到达的世界只是语言的存在。维特根斯坦之后的分析哲学家往往不同程度地遵循上述思路。奎因提出了本体论承诺,但同时又将“实际存在什么”的问题排除在本体论承诺之外,将本体论问题局限于对“存在什么”的讨论,认为后者“几乎完全与语言有关,而存在什么是另一个问题”。(参见奎因,第15-16页)从本质上说,奎因的本体论承诺主要涉及存在的言说和表达。在这里,语言也构成了世界的边界。塞拉斯还谈到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在他看来,人可以创造自己生活的环境,而这种创造也意味着让世界成为“我们的世界”。后者的形成主要与语言的使用和共同的意图有关。创造环境的过程也是基于这个前提。(塞拉斯,2007a,第406-408页)人类世界(“我们的世界”)在这里当然受到注意,但这个世界及其生成主要归功于各种语言活动。因此,塞拉斯进一步认为,素质、关系、阶级等。都属于“语言实体”,“都是语言的表达”。(塞拉斯,2007b,第163页)另一方面,这种观点把世界简化为语言。
与肯定语言是世界的边界相关,是世界与语言的某种重合。在谈到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时,戴维森曾指出:“当我们分享一种语言(在这里指任何意义上的交流所必需的)时,我们也分享了一幅关于世界的图画,就其大部分特征而言,这幅图画必须是真实的。因此,当我们展示语言的大部分特征时,我们也展示了现实的大部分特征。”(戴维森,第130页)语言和世界的图景在这里被理解为一种统一的关系:拥有共同的语言就意味着拥有共同的世界图景;正是这两者的统一决定了语言的特征能够反映现实的特征。这里表现出的内在趋势是把世界变成语言,而当语言和世界图景相互融合时,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很难超越语言:他所达到的只是语言,而不是世界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之外的世界就成了康德所理解的自在之物:在语言成为边界的前提下,人显然很难到达“边界”之外的真实世界。
当然,作为一个人,语言中的世界不同于自然存在:就非自然这一点而言,语言中的世界似乎与现实世界有共同之处。然而,与现实世界由“物”(人作用于物体的实际活动)构成不同,语言中的世界主要是由语言的结构来表现的。当语言成为世界的边界时,它也被赋予了某种形式的起源:世界似乎主要是以“词”而不是“物”为基础的。
现实世界是来源于并局限于“词”还是“名”?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考察“词”(“名”)和“物”的关系。从“字”或“名”本身的起源来看,它的作用首先在于指向现实。荀子所谓的“造名以指实”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见《周易系辞下》)被命名为real,并不仅仅是出于对某个想法的兴趣,而是基于现实的需要。荀子在谈到“名为实指”的意义时,着重从“区分贵贱,区分同异”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同上)“名贵子”是在社会领域发展起来的,而“异”涉及的对象更广,两者都与“物”有关:“名贵子”是指通过社会领域的不同活动,建立一定的人际关系秩序;“辨同异”就是在区分不同事物的前提下,作用于更广领域的对象。无论是社会领域的活动,还是更广领域的对事物的作用,都表现为做事的过程,都为名言(语言)的发生提供了现实的动力。名言(语言)与做事过程的这种联系,也因“事”而表现在“言”上。
语言是关于意义的。就意义而言,语言不仅与所指对象有关,还涉及具体的活动。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理论,肯定了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与早期对语言的理解相比,这一观点更多地触及了人类活动对语言意义的制约。人的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就是做事。在日常的做事过程中,我们可以具体看到语言意义与做事的关系。就施工过程而言,如果其中一个参与施工的工人大声说出“钳子”,同一施工过程的其他工人就会把钳子交上去。这里“钳子”的含义不仅仅是指某个特定的工具,还包括“现在需要用钳子,请上交”等含义。以上场景更形象地展示了语言意义与做事过程的内在联系,具体说明了正是做事过程赋予了“话”具体的内涵。
“词”与“物”的上述关系表明,语言并不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相反,语言从形成到意义的获得,都离不开“物”。语言的这种非本源性也使其难以成为现实世界的最终建构者。分析哲学以语言为基础,显然未能理解现实世界产生的真正前提。
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或存在论哲学和分析哲学虽然表现出不同的哲学走向,但在离开“物”和谈论现实世界这一点上却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如前所述,广义的“物”本来包括对世界的把握和变化,而对世界的把握包括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绝对精神和个体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心”和被定义为存在边界的“语”,并没有完全脱离“物”。但是,上述哲学进路仅仅局限于观念的领域,把做事方式作用于外在对象的实际过程放在了看不见的地方,实质上是通过对事物的抽象消除了事物的实在性。如果说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的特征是把事物变成“心”,那么分析哲学则表现为把事物变成“物”。从现实世界的生成角度来看,这种哲学方法当然注意到了自然事物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但在超越自然存在的同时,又把绝对精神(黑格尔)、个体意识(海德格尔)、语言形式(分析哲学)作为世界的基础,这无疑有异化现实世界的倾向。
人所存在的现实世界确实不同于自然之物,但通过人的活动(“物”)来扬弃存在的自然本性,改变的主要是它的存在方式(从舒适的存在到人性化的存在)。在自然之物获得了它的真实形态之后,它的真实本性并没有被消解。与观念领域中“心”与“言”的单向结构不同,“物”首先表现的是人类对外部对象的实际作用,基于“物”的现实世界在确认其现实性的同时相应地放弃了存在的本质。
原始参考:
[1]古籍:《荀子正名》 《大学》 《韩非子》 《荀子》 《周易》等。
[2]戴维森,1993: 《庄子》,牟波编,商务印书馆。
[3]维特根斯坦,1985: 《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郭英译,商务印书馆。
[4]海德格尔,m .1967,什么是一个事物?由W.B.Barton诉Deutsch,Regnery/Gate Way翻译。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公司。
[5]奎因,1980,从逻辑的观点看,哈佛大学出版社。
[6]w .塞拉斯,2007a,“哲学和人类的科学形象”,载于《理性的空间——塞拉斯文选》,K .沙普R .布兰登编辑,哈佛大学出版社。
编辑:姚远
这个网站是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一键举报。
更多杨荣国简介(历史学家杨国荣简介)相关信息请关注本站,本文仅仅做为展示!